#7.8
日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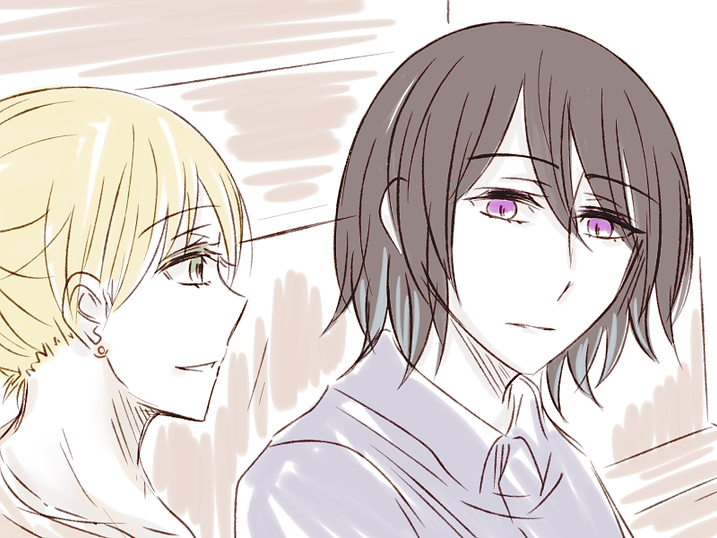
他們是在大學的時候相識的。
他唸法學,她唸歷史,兩者本應互不相交,而他們接觸的契機,是在共同有副修的政治學課上。
在同齡人之間,她所表現出的得體成熟減低了他對周遭庸俗者產生的抗拒感,平易近人的坦然又使他不自覺卸下防御。他們在課堂上逐漸變得熟悉,逐漸變得是那麼位於同窗之上的關係。
她曾經開門見山地跟他說,她對他的接近是經過家族授意的,但是經過相處後、她並不樂於兩人的關係是建立於這件事的擺佈上,所以希望把決定權交給他。
若然這一步也是計謀,那麼這個決定實在很聰明,因為這樣反而給了他們一個發展的機會,亦讓他開始正視起這個叫做艾莉絲泰莉雅的女孩。
她的家族是典型的現代貴族;而他,其實並不是出身在那種歷史悠久的名門,鮮為人知的是,支撐起他的血脈背後的那個名銜是——潘德莫尼。
對於現今這片土地而言,有潘德莫尼就夠了。不是嗎?
而對他的家族——尤其是他的母親而言,為潘德莫尼奉獻生命就是至高無上的榮耀。
所以他,從被生下來的一刻就被決定好未來了。
為潘德莫尼建立未來就是他的未來,就是這個世界的未來。
看著對方,他產生出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。後來,就變成了相知。
他第一次覺得這個世上有理解自己的人。
他跟她訴說了自己並不想走上被安排好的那條路。
「如果有什麼想做的,為何不儘管去嘗試呢?」
「無論你的目標是什麼,我都會支持你。」
「這樣,也許能看著新的歷史被創造出來。不是很有趣嗎?」
於是,他有了支持者,兩人一同割捨身上的束縛,走向新的道路。
離開家族,就等於失去已有的資源。缺乏外力相助,一切的建立都只能白手起家,但是他由衷覺得那段日子,是人生中最充實的時光。
最初的經營起點是顧問公司,作為一個幕後的定位開始考察搜集市場內的資訊;利用在學時建立的人際關係,在合作中展現實力進一步擴建人脈;看準時機豐厚自身的資本,漸漸轉變成主導的一方;收購有潛力的股權,向外攻略擴張轉型,建立起自己的領土。
一切就如他想像中的順利。
很快地,握在手中的權力、可以掌控的東西也變得五花八門了——只是政治這一個區塊,他唯獨不染指。
因為這是他的「家人」想要安排給他的道路。
當初,他們決定另起爐灶的時候,想當然也引來了各自家族強烈的反彈。但是,無論在講求自由法治的社會,還是為了上流階級照顧面子而展現出的大度寬宏,那些人怎麼也無法阻礙他們,只能無可奈何地埋怨著。
這是他的報復。
後來,他與艾莉絲泰莉雅遠走到旁人無法干預的土地上,許下了相守的承諾。
他曾以為,自己也獲得一般人所指的幸福了。
他希望與身旁的人一同見證,那嶄新的未來。
那麼,為什麼最後還是要奪走他所得到的事物呢?
就是因為他對命運的不順從,他對「養育之恩」的背棄,所以遭受到懲罰了嗎?
「我母親生下我之後還陪了我好一陣子呢,她說我們的將來會越來越好的……只是,我好像還是沒等到那個福份。」
她曾經告訴過他,那是家族的遺傳病,但是當時他一笑置之,未曾想過會如此的突如其來——那麼的……無從逆轉。
他自幼便習慣了站在成功的一方,他以為擁有力量,就能夠改寫一切的事情。
他不斷尋求最頂尖的資源,然而只能看著她一點一點的衰弱下去。
「不如……算吧。」
「我想最後在你的眼中,看起來還是好的……」
她的笑容,一如既往的。
撇除疲態,她的神色透露著對他的了然,好像在安撫蠻不講理的小孩一樣。
「我希望你也是……活得好好的。」
「一定會有辦法的。」
他不相信。
卻第一次,鮮明地體會到自己的弱小無力。
*
他用盡了方法都無法取回她。
體內命為瑪爾瑟斯的存在,在宣告的那一刻好像也一併死去了。
如今身後的功名利祿,沒有那個可以分享的人在身旁,已經沒有意義了。但是,在這裡面包含了她對他的期許和心血,所以他必須要讓它繼續活著。
就僅僅是、活著而已。
在最初那個對社會未來充滿期昐的時期,那種心情隨著她的鼓舞而感染到周遭,賦予整個環境人事的體諒和懷柔之情。
現在已經演化成絕對權力的佔領和侵蝕。
再沒有人了解他,他亦不需要了解任何人的喜怒哀樂。
他麻痺在掠奪的實感裡。
然後他遇到了一場精心策劃的佈局。
在飯局上,他盯著眼前這個幾乎與他記憶中的畫面如出一轍的女人。
她……不,「她」的家人還真是看得起他啊。還是說,看得起潘德莫尼與他的關係?
荒謬得可笑也很令人佩服,她的家族為了出人頭地,竟然能鍥而不捨的把親生血脈送上門。某程度上,可說是跟他的「家族」……門當戶對呢。
明知道是惡意的禮物,他還是欣然接受了。
可是每當藉著這樣的行為憶起往事,還是不自覺地、把某部份隨著絕望逝去的感情投射下去吧。
好像那個再也不存在的他還彌留於世一樣。
他緬懷著往昔,妄圖蝶夢莊周。
然而夢境是不堪一擊的。
虛偽的幻象,始終取代不了真實。
甚至不需要自己的干預,後來它便自然而已走到了盡頭。
他嗤笑長醉不醒的自己。
這一場鬧劇,他作為其中一員冷眼地看著。
心裡明明看得很清楚了。
但是他們,憑什麼可以獲得幸福?
那個女人,那個仿冒的次品,憑什麼頂著「她」的臉在他面前演著下三濫的戲,踐踏他曾經的信仰,然後隨心所欲與她的裙下之臣苟且偷安?
這個認知越是清晰,越是提醒他無論再如何力挽狂瀾、終究還是一無所有的殘酷事實;
自己珍視的東西已經永遠地逝去的事實;
自己的努力是多麼的可笑的事實。
他所飾演的慈悲寬宏,他所施捨的視若無睹,這種一塌糊塗的戲碼也差不多該玩完了。
旁人拙劣的掙扎、自己夢回的奢望已經怎麼都沒所謂了。
對於現在的他來說,什麼都不需要了。
這樣的世界,已經不為他所重。
「玩夠了吧,親愛的……『艾莉絲泰莉雅』。」
那天,他從那個不配被映入他眼內的女人身上,撕破了那層噁心的偽裝。在說出那個久未提及的名字時,泯然未覺的情感、埋藏在深處悄然無息的憎念,如冰川一樣消融破裂。
這個神聖的音節被這個不可理喻的荒謬世界、一串跳梁小丑翻弄的段落,深深的污辱了。
沒有了。
沒有了。
什麼都沒有了。
誰在喜悅誰在悲傷都已經不重要了。
沒有人可以獲得救贖。
「那麼,您就放棄這個婚約吧。請不要遷怒他,這都是我的錯。」
「不會,我怎麼會生氣呢,妳的心願,我大可以成全,你養的男人,我也不管你們在這屋裡怎麼廝混,別人用過的,我不屑用,只是——」
「妳就一輩子背負著這裡的名份,做著你們永遠見不得光的齷齪事,無了期的望梅止渴,看著他終有一天捨棄妳而成家立室、哦?或者是我想點法子來讓他垂成之際身敗名裂遷怒於妳,而妳則繼續在這裡錦衣玉食、年華老去——」
所有輝煌的生命都終會被太陽消成灰燼。
一切都毀滅吧。

他蹲下來,最後一次看著亟欲逃離的女人。
「然後一起下地獄吧。」